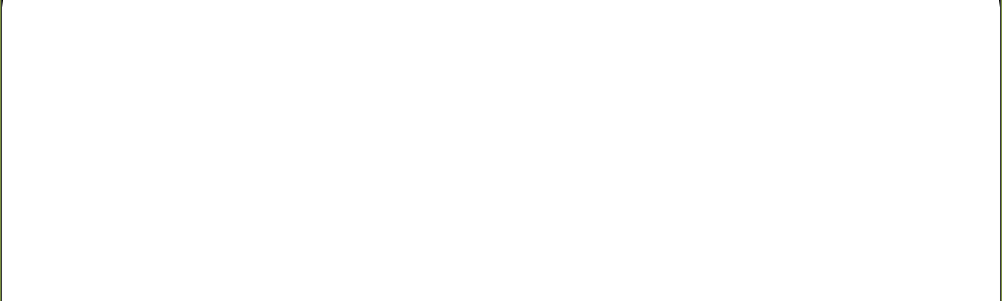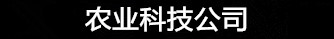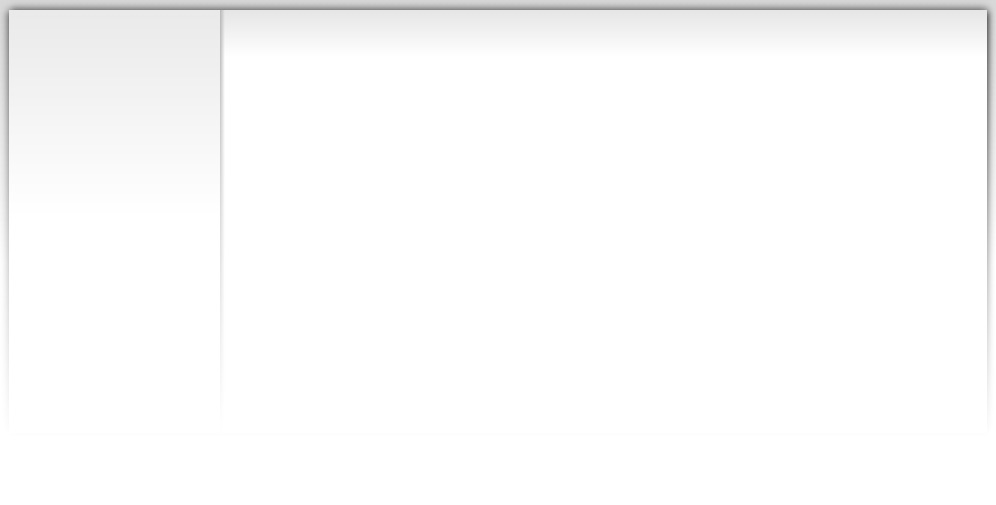
{乐透平台}黑暗真相新城电脑挂机下载。江南人在水乡烟雨的自然环境下,培育驯化、引种栽培各类蔬菜作物,传承发展加工入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江南蔬菜农作体系和丰富的蔬食文化。
文中的江南地区是指狭义江南地区,即明清时期“江南八府一州”: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江宁府、太仓州,地域大约覆盖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及上海大部。
本文重点阐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蔬菜作物的构成、交流传布、结构优化及其历史演进,对该地区蔬菜作物的培育、驯化、引种、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勾勒,丰富区域作物史的内容。
蔬菜作物是对作蔬菜食用、可人工栽培植物的总称,其中既包括已驯化的园圃栽培植物,也包括一些未经驯化但可进行人工栽培的野生植物,自然界的野生植物类食材如海苔菜、石花菜、藻菜等大多不纳入这一范畴。
园圃栽培的蔬用植物是蔬菜作物的最主要构成部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有花色品种丰富的白菜芥菜、历史悠久的瓜瓠茄果、香气各异的姜韭葱蒜,也有由谷入蔬的豆类蔬菜、耐储运加工的根茎蔬菜、品种繁多的水生蔬菜,还有口味丰富、成熟期各异的花色叶菜。
江南人长期开展蔬用作物的选育驯化和中外引种交流,不断优化品类构成,各类播种期、成熟期差异较大的蔬菜作物,尤其适合多茬口栽培,这为江南地区的蔬菜周年供应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叶菜是江南地区重要的蔬菜作物类型,白菜、芥菜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白菜,原产中国,江南地区是多种类型小白菜的驯化地。唐代以前白菜被统称为“菘”,但并非所有“菘”均代指白菜,有时一些其他蔬菜也被称为“某某菘”,如“温菘”“紫花菘”均代指今日之萝卜。
到唐代,依然没有有关菘的具体品种的区分,但其变异性强的生物学特点已被观察记载,“菘菜……所生土地随变”。清代方志也印证了这一特点,“白菜,岀郡东门外者嫩白最佳,移种他处则为青菜、油菜,在昔如此”。
江南地区的青菜、白菜、油菜、藏菜等多属后世之小白菜,江南地区的大白菜则被称为“黄芽菜”“黄矮菜”。
芥菜,原产中国。芥作蔬菜食用时多制作成干菜或盐菹,“芥为咸、淡二菹,亦任为干菜”。唐代以前的有关芥菜品种的记载较少,北宋时增多,宋苏颂《本草图经》载:“有青芥似菘而有毛,味极辣;紫芥,茎叶纯紫可爱,作齑最美……其余南芥、旋芥、花芥、石芥之类,皆菜茹之美者,不能悉录。”
明代以前,江南地区芥的栽培较为稀少,宋(嘉泰)《吴兴志》、《会稽志》仅载有食苔的大叶芥和食子的子芥,宋(咸淳)《临安志》载:“芥,紫而辣者难得”,明《嘉善县志》物产也载:“芥,菜之贵者,其味辛。”
江南地区芥菜种类的增加大约发生在清代,出现了许多蔬用芥菜品种,如白芥、银丝芥(佛手芥)、荷叶芥、鸡脚芥、紫芥、猪肝芥、黄农芥、冬芥菜、弥陀芥、青芥、油芥等。芥适合加工贮藏,能显著延长蔬菜供应期,因此也成为当地重要的淡季佐餐蔬菜。
江南地区还有多种其他花色叶菜,由于叶片水嫩易腐,不耐储藏,且无确定的成熟采收期,适合按需随时采收,因此此类食材也是百姓日常的鲜食蔬菜,如菠菜、葵菜、苋菜、生菜、甜菜(莙荙)等。
此外,一些滋味特殊、采收期短、产量低、富有特色的稀有叶用蔬菜,也是江南应季蔬菜的组成部分,如青芹、茼蒿、芥蓝、金花菜(黄花苜蓿)、苦荬、枸杞、甘菊等。其他还有一些“不植而野获”的山野佳蔬类叶菜,如荠菜、薇等。
江南地区常见的根茎类蔬菜主有萝卜、山药、芋、蔓菁,明清时期,新增番薯、马铃薯等。此类蔬菜适合加工、耐储藏,且除萝卜、蔓菁之外,大多淀粉含量偏高,可粮菜兼用,补充荒年粮食的不足。
萝卜和芋是江南地区最常见的根菜。太湖的萝卜品质优良,有“太湖萝卜赛过金坛藕”的美誉。江南地区的萝卜品种丰富,崇祯《乌程县志》载“春末生者谓之杨花萝卜,形细长;夏生者为夏菘萝卜,形圆;秋生者为秋菘萝卜,形长而大,俱出太湖旁。”春播、夏播和秋播萝卜品种可组合搭配播种,错时上市。
江南地区的芋、山药也有多种品种,光绪《剡源乡志》记载:“芋,有乌脚芋、黄粉芋、大芋、奶红芋、奶香芋数种。”《东林山志》也载有香羹芋、红沙芋、白梗芋、青头芋等。山药,又称薯蓣,江南太湖湖滨平地种植的山药肥大而味美,其中形状如佛手的佛手山药最有特色。
明代,嘉定地区的山药据其口感又可分为粳种和糯种。此外,香芋、黄独等也是江南的特色根茎类蔬菜,蘘荷(甘露子)、百合、胡萝卜、莴笋,以及杜笋、鞭笋、燕来笋、茶笋等各类竹笋也较为常见。
豆类作物早期被统称为菽,以收获籽粒为主,归入谷类作物,明《汝南圃史》载“黄豆、紫罗豆、黑豆、菉豆、赤豆俱谷类,圃中难植,故不入史。”但由于一些豆类嫩荚适合蔬用,因此被逐步引入园圃栽培,最终被移出谷类而转入蔬类,形成了独立的豆类蔬菜作物大类。
江南地区由谷入蔬的豆类主要有毛豆(青豆)、豇豆、豌豆、蚕豆、刀豆、扁豆等。这一转变过程在方志中有多次记载,如光绪《平湖县志》特意将白扁豆、香珠豆、赤豆、豇豆、刀豆、野鸡斑划入蔬属。虽然豆类在由谷入蔬的转变过程中,方志记载时对其归类属性仍多有反复,但其蔬用特性总体上还是逐步得到了明确和认可。
江南地区栽培食用瓜瓠类蔬菜的历史由来已久,早期主要以栽培瓠匏为主,人们早已认知和掌握了“甘瓠苦匏”的规律,“叶叶瓠、猪头瓠、合盘瓠可食,捏头瓠、研茶瓠不可食”。
宋元时期,江南瓜瓠类蔬菜主要有瓠、葫芦、梢瓜、黄瓜、冬瓜等,丝瓜则先载于医书,后归入蔬类,宋医书《卫济宝书》中有丝瓜汁、丝瓜灰入药的记载,《全芳备祖》将其载入“菜部”。
明代以后,江南瓜瓠的品类有所增加,明万历《嘉善县志》载有甜瓜、冬瓜、西瓜、筲瓜、王瓜、丝瓜、瓠瓜、苦瓜(錦荔枝)、南瓜等,并按食用方式不同进行归类,如适合酱制、熟制的酱瓜类,适合生食的甜瓜类,可充粮度饥的南瓜类等。
古代江南地区的茄果类蔬菜品类稀少,明代以前主要以青色、白色、紫色三色茄瓜为主。明代以后,番茄、辣椒传入江南地区,但也并未马上成为蔬菜作物,清代末期才开始逐渐走上普通江南人家的餐桌。
江南地区的香辛菜主要包括韭、葱、蒜、薤、姜、芫荽、紫苏、薄荷等,其中,韭、葱、蒜、姜是栽培最多的品类。韭菜是最主要的叶用香辛类蔬菜,露地栽培时,一年中除冬季以外,可随时采摘食用。
江南人还利用其生长特性来延长采收期,形成春食韭菜、夏食韭苔、冬食韭芽的周年供应。“韮……隆冬摘芽如鹅黄,色质脆味鲜,他方所无”。
葱、蒜、薤、姜是重要的调味类蔬菜作物,这些味道浓郁的香辛菜在江南地区被广泛用于鱼虾蟹的烹饪制作,起到去腥提鲜等的作用。
与北方甜葱作蔬直接食用不同,江南地区的葱主要用来调味,品种有吴葱、台葱、细香葱,以及胡葱、山葱、龙爪葱等。
同治年间,上海又新增一种根如小蒜、叶细如野生葱的地葱,也称葛葱。蒜有大蒜和小蒜,冬春食青蒜,夏季食蒜苔,旺季多余蒜苔还可腌制为佐餐小菜。
薤是中国的传统蔬菜作物,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薤已很少用于家庭食用,而多见于祭祀场合。明《江阴县志》载:“一种似韭而大,名薤,礼祭宗庙。”
此外,芫荽、薄荷等因味道独特浓郁,多用来点茶食用。辣椒在明代传入江南地区,先作观赏植物用,后因其辛辣调味功能强,被广泛用于辛辣调味和蔬菜加工。
江南地区水网密集,湖滨湿地较多,盛产各类水生蔬菜,如莲藕、菱、茭白、慈姑、荸荠、芡实、荇菜、莼菜、芹等。
宋代以前,莲藕、菱、茭白等是栽培最多的水生蔬菜;茨菇、荸荠、芡实次之;荇菜、莼菜、野芹等多为野生,鲜有栽培,食用也并不广泛,“芹,生水边,断之亦甚香,今唯文庙丁祭用之,人家采食者则甚少。”
到清代,新品白芹才逐步发展为腌渍类栽培蔬菜,“今乡土种惟白芹,冬至后作菹,甚甘美,春后不食”。荇则主要用于泡酒或制作小吃,“荇,野人以采粉作糕,美如饴蜜”。
此外,一些原产域外的新品蔬菜于明清时期传入江南地区,如番茄、辣椒、菜豆、花椰菜、结球甘蓝(卷心菜)、玻璃生菜等,但起初栽培食用并不普遍,只在局部地区的个别园圃中试种或用作观赏用,到清末民初才逐渐传播开来,成为餐桌上的新品,并逐步发展成为江南蔬菜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南地区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各类植物的生长,经过长期的人工培育和选择,发展出了类型丰富、口感不同、成熟期各异的蔬菜品类。
到明清时期,主要用于园圃栽培的蔬菜约三十余种,瓜菜类有丝瓜、南瓜、北瓜、冬瓜、菜瓜、黄瓜、苦瓜、瓠匏;豆类有豇豆(裙带豆)、刀豆、扁豆、龙爪豆;茄果类有茄;叶菜类有白菜(小白菜、菜薹、大白菜)、芥菜、甜菜、菠菜、生菜、香芹、茼蒿、苦荬、蕹菜;香辛类有葱、蒜、韭、姜、芫荽;根茎类有萝卜、胡萝卜、大头菜、蔓菁、莴苣、笋、芋、山药、红薯;水生蔬菜类有菱、莲藕、茭白(菰)、慈姑、荸荠等。
各类花色蔬类的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是江南园圃栽培蔬菜的重要特色。不同类型蔬菜作物的播种时期、采收部位和成熟期差异较大,有利于排开播种,错时采收;同类作物中性状差异较大的不同品种,也可适应不同茬口的栽培需要,如小白菜中既有适合正月播种的看灯菜,也有适合七八月移栽冬季采收的冬旺菜;有适合盐渍过冬的京口菘,即箭杆白,也有适合春季抽薹、干物质含量高、适合作菜干的越冬栽培盘棵菜等。
江南蔬菜作物的这一特点在各类古籍中均有所记载,如《浙江通志》载“湖地宜菜,四时皆有,冬春为市,而冬月尤多”。
陆游诗云“吴地四时常足菜,一番雨过一番生”。丰富的作物品类为江南人开展蔬菜的四时栽培供应提供了多种选择。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蔬菜不仅品类多,而且品质优良,鲜食与加工具佳,鲜食如炒食、羹汤;加工储存如盐渍、酸制、糟制、发酵、干制等,方式多样,不一而足。芥菜类、根菜类、瓜菜类等都是常见加工储存品类。
芥菜是江南地区“白菜之外惟此菜最多”的蔬菜作物,加工食用方法多样。南宋常州《毗陵志》载:“芥,有紫芥、黄芥,惟苔心最辛脆。”明《苏州府志》载:“芥菜,季春则长薹心,长尺余,大如指,吴人则盐藏瓶瓮中,夏秋方食。”
此外,根用芥菜也多用于加工,“大头菜,芥之属也,其根如萝卜,以炒盐茴香制之,香脆异常,惟上元、江宁二邑有之,四方用相馈遗。”一些芥的加工品还成为著名地方特产,流传多年,如上海顾氏芥菹始于清康熙年间,百余年之后,到嘉庆年间仍为“他郡所无”之上海特产。
瓜瓠类也是最为常见适合加工储藏或鲜食的品类。甜瓜嫩时生食坚脆,老熟后酥美,可酱渍为酱瓜,冬瓜可以做汤或蜜浸,筲瓜可生吃或醃藏等。《春秋佐助期》载:“八月雨后,瓜菜生于洿下地中,作羹臛,甚美。”
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糟藏瓜姜还曾为贡品。其他各类蔬菜的盐渍和干藏工艺成熟,供应期较长。《沈氏农书》载:“腌齑菜、萝卜菜、苔心菜,每百斤用盐三斤,踏过,石压,二十日后取出,晒干……入坛收藏。”适合此类加工方式的主要有萝卜、薯芋、姜、茄、蒜、笋等。
江南地区的蔬菜作物与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从蔬菜作物的命名到蔬用食材的生产加工利用,从园圃景观、园圃艺文到蔬食产业、蔬食习俗,形成了丰富的蔬菜园圃文化。
江南人在进行蔬菜命名时,融入了大量的生活文化,用最生动的方式记载和反映了蔬菜植物的形状、口感、生长习性。
这些名称中有刻画蔬菜生长性状的“黄矮菜”“箭杆白”“赤根菜”“紫芽姜”“羊眼豆”“马齿苋”“佛手芥”“裙带豆”“挟剑豆”“龙爪葱”;也有描述其栽培特点的“春不老”“沿篱豆”“辰瓜”(冬瓜)“燕来笋”;还有蕴涵丰富故事传说和生活智慧的“诸葛菜”“菜伯”(葱)等。
这些富有特色、妙趣横生的蔬菜命名文化体现了江南人善于观察总结,能准确掌握作物生长、生活习性规律的能力。如一种芥菜被命名为“雪里蕻”:“四明有菜,名雪里蕻,冬月,雪深,诸菜冻损,此菜独青。”
吴语“蕻”的意思是指草木萌芽,“雪里蕻”一词即生动描述了此类芥菜极强的越冬抗冻能力。再如,太湖地区的“龙爪葱”,获此名称是由于此品种葱以气生鳞茎繁殖,即花茎顶部生出几个小气生鳞茎,继而发育成多个环生小葱,又在小葱的顶芽上再环生小葱,观如龙爪,又如盖楼,所以人称龙爪葱、楼葱、天葱。
江南地区的蔬菜园圃文化还体现在岁时节日中。特殊的蔬菜饮食成为江南人日常的生活习俗和深刻的乡土记忆,苏东坡诗云“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簇春盘。喜见春盘得蓼芽,蓼芽蒿笋荐春盘。”立春前,用各种新鲜蔬菜组成“春盘”,举行“荐春盘”活动是当地人迎接新春的重要仪礼。
一些独特的蔬食菜品也成为岁时祭祀物或过节必备美食,如苏州、无锡等地过寒食节必用青团、熟藕、茄饼等蔬食。错落有致的园圃景观和常见的园圃生产活动还常常成为诗人的吟咏对象,体现出人们对恬淡人生的价值追求,流传千古。
陆游《观蔬圃》诗云:“菘芥可菹芹可羹,晚风咿轧桔槔声。白头孤宦成何味,悔不畦蔬过此生。”范成大也在《冬日田园杂兴》中写到“拨雪挑来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布衣蔬食,栽瓜种菜的园圃生产已然成了悠然园居生活的文化象征。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蔬菜作物的丰富品类,部分来自本地培育的传统优良农家种,部分从周边及其他地区引入,还有一些是原产欧洲、美洲的蔬菜品类,多途径传入中国后,逐步扩展到江南地区。
在蔬菜作物的传播交流过程中,一方面,传统的本地白菜、芥菜、萝卜等始终处于主要地位;另一方面,不同时期自外地传入的新品,如蕹菜、芥蓝、大白菜、大头菜,以及南瓜、番薯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本地化适应后,也逐步在江南形成了新的传布区。
在蔬菜作物的优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引进的蔬菜由于产量和商品化程度较高,逐步发展成为江南地区蔬菜花色品种的重要组成;同时,一些本地原产,但口味较为特殊,或商品化生产优势较弱的品类,则逐渐减少甚至被淘汰出蔬菜作物序列。
江南温暖湿润的自然条件有利于作物的选育与改良,传统品种经过长期的驯化栽培,发展出了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优良品种。如,江南地区的小白菜细分品种有牛胫菘、乌菘、青菘、白菘、蚵蚾菘、瓢儿菜、箭杆白等。
明代,还培育出水白菜、春菜等早熟种。丰富的小白菜品种适合分期播种,有利于错时应市,因而被广泛栽培,万历《嘉善县志》载“禾人以此为业,白曰白菜,青曰青菜”。
除了在当地栽培外,这些传统优质品种也向周边地区扩散传播,宋杨万里《进贤初食白菜,因名之以水精菜二首》诗云,“灵隐山前水精菜,近来种子到江西”,记载了杭州的优质白菜品种传播到江西的历史。
在芥菜、萝卜等传统品种的发展过程中,江南人根据不同可食部分的特点进行选种、留种,培育出了多种口味鲜美、适合加工的优质品种。如湖州“雪里蕻”、上海“银丝芥”等芥菜品种,同治《湖州府志》载“雪里蕻,一作春不老……腌藏之,尤嫩而美。”光绪《嘉兴府志》载:“芥多种,以春不老为第一。”再如萝卜,江南地区的水土尤其适合其生长,除传统的优质大白萝卜外,当地还培育出一些新品,如颜色特殊的南京紫萝卜,“萝卜,南京有紫赤皮者,他处皆白”,可食可玩的“大红袍”,“芦菔……今有一种小而圆,红色绝艳,可作供玩,与水芦菔同熟,皮厚味辛,腌作蔬最脆”。
传统农业时期,作物的引种传播大多经历了物种自然扩散的过程,且由于地理、气候和饮食习惯的差异,一些作物往往还会经历多次反复引种传播、适应与淘汰,才能逐渐在新区域发展为优质品种。
中国南北人口流动频繁,一些北方优良蔬菜作物随之传入南方,光绪年间,山东胶州大白菜被引种到江南地区,取得良好的商业效益,收益甚至好过当地原产的小白菜。“吾得山东胶州白菜,种之于地……价较油菜等数倍。”再如,山东聊城的优质大头菜引种到嘉善后,加工成干,可作为夏季蔬菜的重要补充。“大头菜,出邑之西乡,嘉庆初年,乡人得东昌之种,八月下种,二月掘根晒干为菹,夏间出售甚广。”
北方南传的传统品种还有优质的瓜类蔬菜,如北方黄瓜及一些甜瓜品种,如蜜筩瓜、雪瓜、水晶瓜等。
由于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环境条件差异较大,北方传入的蔬菜作物需要经历一个环境适应过程,因此出现“携北方黍稷及蔬菜之类至南方种植者,多不收获”的现象。
同时,蔬菜作物传入后,除适应新的气候水土之外,还需与当地的饮食文化交融发展后,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如叶用甜菜早在宋代已引种到江南地区,但到清代,在太湖地区的种植食用依旧不甚广泛。
闽粤及周边地区人口向江南地区的流动也促进了一些优质蔬菜作物向江南地区的扩散。研究发现有多处方志记载都客观反映了这一物种扩散传播过程,如南宋《吴兴志》载:“甜菜、蕹菜、莙荙,近来自他郡,人亦稍有种者”。
康熙《松江府志》载“紫花芥,……近岁吾乡始有之。”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方志中的相关记载进行统计还发现,蔬菜作物的扩散往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品种的多次传播,并且在地理上由近至远进行扩展。如闽粤原产芥蓝多次入传江南,嘉庆《松江府志》载“芥蓝……闽中有之,近岁闽人携其子艺之学圃,遂传郡中。”
一些文人笔记也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如清《浪迹丛谈》载:“芥蓝菜,本闽产蔬品中之最佳者,而他省无之,然吾乡人仕宦所至,率多于廨中隙地种植。”再如,在方志中还可见到原产闽粤地区的蕹菜,逐渐向北传播至浙南后,再继续北上传入太湖地区的过程,“蓊菜……种出浙南,今处处有之。”“空心菜……亦客民带来者。”
周边地区优良蔬菜品种向江南地区传播,除了品质口味的原因外,有些也是蔬菜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安徽山区的优质高产姜种被引种到常州地区进行商品化生产,“姜,种出自宣城,县民多种之以为利。”
区域内蔬菜品种的扩散还促进了蔬菜加工产品的发展,并进一步促进了对新品蔬菜的引种,如“罗汉菜,向惟嘉定乡间有之,近日沪地园圃中丛生甚众……沪人腌之为菹杂,以青果装瓶,以贻远客,味甚美。”
引种域外原产蔬菜作物是江南地区蔬菜品类增加的另一途径,沿海港口地区多为域外作物传入中国的初期落脚区域。宁波、舟山、上海等均为江南重要港口,对外交流甚多,一些优质蔬菜品类随商旅直接进入江南地区,如辣椒、玻璃生菜、番茄、西芹、花椰菜、洋葱、洋芋、洋瓜等。
另有一些品种传入南方闽粤和东南亚后,进一步北上传入江南地区,如原产美洲的南瓜与番薯等。
番薯于明代首次传入江南地区后,又有不同地方的品种多次传入,其中既有自东南亚经闽粤传入,也有直接自日本、菲律宾等国传入的。如嘉庆《吴门补乘》载“山芋,本名番薯……本出吕宋国,渐及闽浙,今吴地亦有之。”明代《普陀山志》载:“蕃薯,种来自日本,味甚美”。清光绪《定海厅志》载:“甘薯……南方以当米谷,种出交趾……今有紫皮白皮二种,紫皮者肉亦带紫。”清《双溪物产疏》载“山芋……闽人始教湖汊山中人种之”。
晚清,来华西人渐多,西餐食材需求增加,与中餐蔬菜熟制食用不同,西餐蔬菜大多生食,中国以粪肥等方式栽培的蔬菜难以满足其要求,两者的品种选育目标、栽培要求差异较大,此期,适合西餐的生菜、番茄、西芹、甘蓝等品种被大量引入中国,一些西人还自辟菜园进行生产。
同治《瀛壖杂志·上海县》载“北郭外,多西人菜圃。有一种不识其名,形如油菜,叶青翠可人,脆嫩异常,冬时以沸水漉之,入以酱,即可食,味颇甘美。”
从其所载生物学特性看,此新品蔬菜为玻璃生菜(今人称生菜),即叶用莴苣。同期,一些产量高、收益好的“洋”品种也传入江南地区,如洋葱、洋芋、洋瓜等。民国《南汇县续志》载:“洋西瓜,光绪初年,始有此种。”
这些域外蔬菜作物引进后,适应当地风土环境,演化出了新的分布区,栽培面积也不断扩大,清末《上海乡土志》载:“自通商以来,而洋葱、洋芋艿等产额颇巨。”口味优良、耐储运品类的入传,对后世江南蔬菜作物的商品化、规模化生产和实现周年供应影响较大。
古代江南地区蔬菜作物的引种优化过程也是一个对弱势品种的选择淘汰过程。蔬菜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以及产量、成熟期、储运特点等因素直接影响着蔬菜作物的发展与淘汰。
一方面,一些适合规模生产、能够提前或延后上市、商品化生产特性强的类型被保留,并广泛传布;另一方面,一些产量低、可食用部分小、采收期短、不耐储运,商品性弱的类型则越来越少甚至被淘汰。
在这一过程中,蔬菜的食用品质和商品品质始终在相互博弈,有时候一些本地传统品种以其优良的口味对新传入品种产生竞争压力,如,清《松江府志》载:“茄,陈志俗名落酥,有紫白二种,吾乡所尚以白皮为贵,味甘嫩,胜于客种。”
有时候一些口感优良的传统品种也被新传入的口感较差但商品性好的品种所淘汰。如清《嘉定县志》载“山药……出北乡者佳,形扁质细,肥香无滓,近土人牟利,多栽太仓之种,但取其大,味稍减矣。”
口味不甚佳、产量高的太仓种就以其突出的商品性淘汰了口味更优的北乡种。总体上,蔬菜的规模化、商品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蔬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发展,如同治《湖州府志》载“芋有六种,今乡土多种白芋”。事实上,这一现象在当代蔬菜产业化生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一些蔬菜作物由于口感口味特别,或含有特殊营养物质,或具有药效不宜长期大量食用,在选育过程中则逐步被淘汰。如防风,又名山花,在宋代尚列入优良蔬菜品类,甚至还曾入列贡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十三载“山花,或曰防风,苗茎织弱而长,味甚甘脆……尝有赋”。元明之后,防风被淘汰出蔬类,列入中药材序列。
汉代以前,江南地区地广人稀,农业生产长期处于火耕水耨的水平,作物的培育驯化能力尚弱,园圃蔬菜作物的品类十分有限。三国时期,孙权迁都建业(今南京)后,大力开发江南地区的农业,包括蔬菜作物在内的农作物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或驯化培育本地作物,或引种、试种栽培其他地区的新品种,江南地区的蔬菜作物品类不断增加。
史上南北人口的流动、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蔬菜作物品类的传播与重新分布。蔬菜作物的品类结构优化和蔬菜栽培加工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蔬菜园艺水平的发展提高,为实现蔬菜产品的相对充足供给和蔬菜的周年供应提供了技术条件。
江南人采摘和栽培利用蔬菜作物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考古发现,距今约6000年,属于崧泽文化遗址的上海青浦金山汶遗址,距今5300—4200年,属于良渚文化遗址的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均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葫芦籽、瓠瓜籽;浙江湖州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甜瓜子,这些证据表明,江南地区的先民采集或栽培甜瓜、葫芦、瓠瓜、菱角等瓜果类蔬菜作物的历史可溯及新石器时代。
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本味》载,“菜之美者……具区之菁”,具区指太湖地区,菁在古代一般代指芜菁、萝卜、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可见当时太湖地区的十字花科蔬菜已是公认的美味栽培蔬菜,时至今日,太湖地区的白菜、芥菜,湖滨夜潮地的白萝卜等依然是中国十字花科蔬菜的优质品种资源。
三国时期,人们栽培瓜瓠类供食,但生产供给尚不充分,《吴志》载:“步骘……世乱,避难江东……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
南北朝时期,南方蔬菜品类有所增加,其中既有葵、蓼、杞、菊、荠、苜蓿等采摘野蔬,所谓“蒿荠之类多野采”,同时也有韭、菘之类的园圃栽培蔬菜。《齐书》载,周颙隐居钟山,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可见当时经过人工驯化选育栽培的蔬菜,其品质较野菜更胜一筹,也更为珍贵,“早韭晚菘”也一度成为园圃栽培蔬菜的代名词。
南朝梁武帝尚佛,以蔬食为主的素食文化在江南地区流行,全国弃荤改素,连寺庙荐馐祭祀也改用蔬类,江南地区的蔬菜作物得到新的发展,园圃栽培蔬菜渐多,在城市周边也出现了少量专门种菜的园圃,《梁书》载,范元琰因“家贫,以园蔬为业……见人盗其菘菜……”。从总体上看,魏晋之前,蔬菜作物的生产供应尚不充足,还处于从野采与人工栽培并重逐步向以园圃栽培为主发展的过渡阶段。
唐宋时期,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江南快速崛起,尤其宋室南渡后,江南人口聚集,城市发展速度加快,江南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取得新的发展,蔬菜作物品类出现明显的增加,城市周边的蔬菜生产也趋于专业化和商品化。
据宋《建康志》《重修毗陵志》《重修琴川志》等江南方志记载,叶菜类、豆类、果菜、瓜类等成为当时最常见的园圃栽培蔬菜,城市周边园圃十分普遍,可谓“田塍莫道细于椽,便是桑园与菜园”。湖滨水汊也多有人工栽培的水生蔬菜,“滨湖多植莲藕菱芰茭芡之属”。
据宋《梦梁录》载,南宋都城临安已形成了专门供应城市的蔬菜集市,即所谓“东菜、西水、南柴、北米”。由于部分蔬菜生产的收益比粮食作物更为丰厚,“茭田之直可十余金,利倍禾稼”,因此出现了规模化生产蔬菜的现象,一些蔬菜甚至被长途贩运到其他地区销售,宋《武林纪事》载“杭城东园人家,四时种菜,贩卖远至临平长安,俱船载而去”。
有些豪门望族人家园圃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自给,但开展专业化蔬菜栽培则多有盈余,也可以出售,“秦淮河南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买菜得钱三万……元景怒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尔乃复卖以取钱,夺百姓利邪……”。
这一时期,园圃栽培蔬菜的重要技术进步是对蔬菜品种的区分趋于细致,人们按作物栽培周期区分出“台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或按性状等区分出“青菘、白菘、蚵皮菘”等白菜品种;按性状和口味区分茄子品种“乡土有三种,有紫茄,有白茄,有水色茄,色亦白而甜嫩,可生食”;按颜色和取食部位区分芥菜品种等。
对栽培品种的细致区分为后来蔬菜作物的引种交流积累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唐宋时期,园圃蔬菜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发展趋势也促进了蔬菜新品种的引种传播,在江南地区的方志中,可以看到各地多次从他郡新引种菰白、蔓菁、菠薐、芸台等进行商品性试种的历史记载。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繁荣发展,人们对蔬菜花色品种和口感口味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了增加供应,一方面从本地传统蔬菜中驯化选育优良品种,另一方面从外地引种优质蔬菜品种类型,提高蔬菜的供应质量。
同时,通过优化品种、错季栽培,科学协调蔬菜播种收获与加工贮藏环节,有效延长了供应期,基本实现了蔬菜的周年供应。综合梳理各类方志、农书的相关记载发现,江南地区自一月到腊月,几乎每月都有不同品种蔬类作物的播种、采收和加工(表1)。
明《赵氏铁网珊瑚》“梅花道人墨菜卷”诗云“老圃佳蔬日应长,菁青苣紫韮茁黄”,“食肉终易厌,菜根滋味长,黄齑三百瓮,日日食家常”,反映的正是江南地区的日常蔬菜生产与加工供应状况。
古代,由于人工有效控制气温、光照、水分等要素的手段和条件有限,实现蔬菜生产的周年供应难度大,需要巧妙利用天时、地利等条件,并充分发挥轮作、间作、套种以及采收、储藏、加工、运输等技术环节的调控作用,才能减少蔬菜的淡旺季影响,提高周年供应的能力。在品种优化方面,江南人已能根据播种时间、植株性状、加工方式等条件选育出不同的品种满足生产需求。如选育出的蔬菜品种有的适合鲜食、有的适合干制、有的供应周期较长;有的可越冬栽培春季采收,还有的采收期可晚至四月,有的可供冬季鲜食等。
其他各类蔬菜也均有较为细致的品种区分。在栽培安排方面,人们熟练掌握了园圃作物的间作套种技术,能够科学安排前后茬口。如,麻与萝卜的轮作;桑园中百合与香芋的间作,“桑园间种百合,根甘美,花芳洁……香芋亦然”。人们还能巧用篱笆、墙角等零碎地栽种多年生蔬菜作物,“篱下种山药,根常留,每年食其枝(根),力不劳而得味多”,“篱下种萱花,自生自长,花开随采以晒,亦蔬之辅佐也。”
人们还注意科学取舍,充分利用蔬菜作物的可食部分,如“甘菊性甘温……春食苗,夏食英,冬食根”。在园圃土地利用方面,通过“秋收筑场,春天种菜茄”,实现“园中菜果瓜蒲,惟其所植,每地一亩,十口之家,四时之蔬菜,不出户而皆给”。
在采收、加工、储藏方面,人们通过蒸煮、晾晒、盐渍、干制、泡制等方法,将旺季蔬菜保存下来,保障淡季供给。春季制干菜,同治《湖州府志》载“乌菘菜,春间煮晒为干蔬,可供半年之食。”夏秋季播种的白菜,收获后可以酸制或盐渍,供应秋冬季食用。“菘菜……晚者为藏菜,味脆而腴,盐藏以御冬,比屋皆然。”加工蔬菜在淡季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蔬用食材,此期常见的加工蔬菜有咸瓜瓠、黄豆黑酱、糟茄子、漕姜、盐蒜头、盐蒜苗、盐菱拇、蒜渍丝瓜、盐齑菜,茄干、芦葡菜干、苔心菜干、菱实、芡实、豆豉等。一些加工蔬菜作物还发展为当地重要的特产,如杭州施氏酱瓜、镇江酱菜、嘉兴萝卜条、嘉定罗汉菜等。
先秦时期《黄帝内经》“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明确了谷类粮食为摄入食物之首,其次为果实、肉类,而菜蔬则排在最末,为补充之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掀起民间食素风俗,蔬菜作为素食的最主要食材,其重要性逐步上升;南宋时期,临安的餐饮业中已有专门经营素食的餐馆;清代,薛宝辰所著的《素食说略》中涉及五十余种蔬菜作物;民国,孙中山为食素先行者,倡导素食文化……如今,在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中,蔬菜位于饮食结构金字塔的下部,其对人口供养质量的影响日益显著。
区域蔬菜作物的品类发展史也是一部蔬菜作物的引种传播史。纵观其过程,可以看到作物的引种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主要包括两种,即扩展传播和迁移传播。扩展传播主要是指物种从起源地由近及远向外的连续扩展,在扩展传播过程中完成对地理、气候、风土的本土化适应和物种的生物进化。
如国内蔬菜作物的南北、东西双向连续传播,海外作物经欧洲、印度、东南亚、闽粤等地逐步向江南地区的传播,都属于此类传播方式。迁移传播则主要是指通过人口大范围空间迁徙,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进行跨越式传播,如移民、商旅、官旅及其他热心人士在远距离迁徙或旅行过程中携带种子,跨越较大地理空间进行的偶然的、非连续性的传播。
在中国南来北往的商路上,海上、陆上丝绸之路上,均发生着此类物种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由于物种缺少在区域内的连续自然扩展的适应过程,加之种质的特异性强,受作物的产量、抗性等商品性因素影响大,所以单次的传播效率不高,往往要经过多次传播,才能在目的地扎根。综合各类记载发现,江南地区的蔬菜作物品类结构的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区域外蔬菜品类的反复引种驯化的过程。
影响区域蔬菜作物品类与品种优化的因素很多,既有物种的扩散传播等内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外因,如人口流动、消费增长、商品化、专业化生产发展趋势等,其中,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具有驱动作用。
江南地区是古代中国国家经济政治重心南移后的重要发展区域,人口不断聚集,六朝时期发展出了首个人口逾百万的建康城;后来南宋定都杭州,大运河及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南方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其发展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元明清时期,对南方经济的倚重促进了江南市镇的快速的发展;清末,上海开埠,江南又成为中西文化的重要交汇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口流动增长、蔬用食材消费需求的增长、人口供养质量需求的拉动、园艺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粤闽毗邻地区和东南亚及海外其它国家的物种交流等因素,综合推动了古代江南地区的蔬菜作物品类和品种数量的优化发展,促进了江南地区蔬菜园艺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江南地区蔬菜作物的发展进步,不仅丰富了江南人民的餐桌,健康的蔬食习惯和丰富的蔬食文化也辐射、影响和改变了国人的蔬菜饮食习惯,为提高土地的人口总体供养质量提供了必要条件。
同时,各地蔬菜作物的交流传播刺激和促进了蔬菜园艺科技的发展,使得蔬菜生产业逐步上升成为区域和国家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作者:丁晓蕾,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作物史、农业科技史;李静华,硕士,淮安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研究助理。